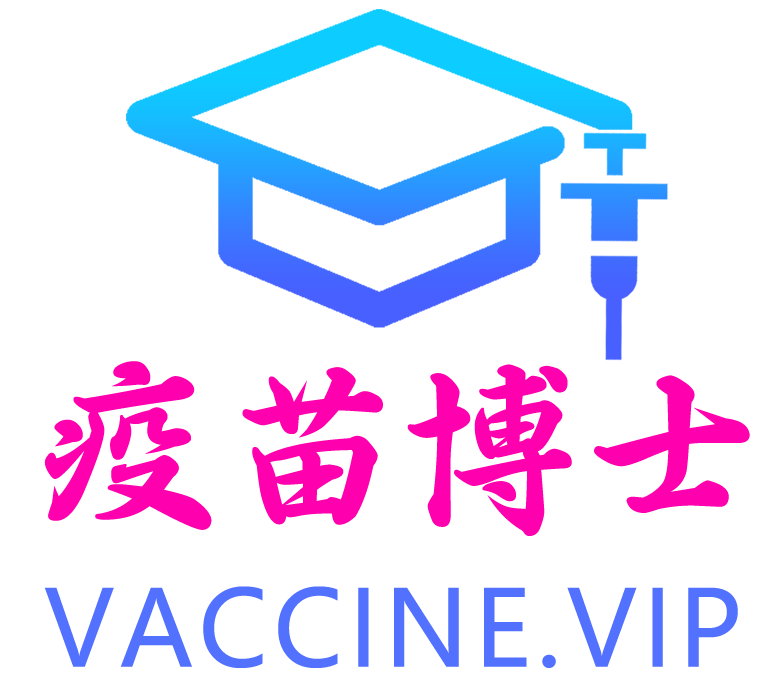Contents
Vaccines against tick-borne encephalitis: WHO position paper – 2011
依据为各成员国提供卫生政策方面指导意见这一职责,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就预防具有全球公共卫生影响的疾病的疫苗及联合疫苗问题,发布一系列定期更新的立场文件。这些文件着重关注疫苗在大规模免疫规划中的使用,归纳了各相关疾病与疫苗的基本背景信息,并就如何在全球使用这些疫苗表明了世卫组织目前的立场。这些文件经过世卫组织内部和外部众多专家的审阅,并且自2006年起,由世卫组织的免疫战略咨询专家组(SAGE)审核和认可。1这些立场文件主要供各国的公共卫生官员和免疫规划管理人员使用。不过,对这些立场文件感兴趣的还可能包括一些国际资助机构、疫苗生产企业、医学界、科学媒体和公众。
这是世卫组织关于蜱传脑炎疫苗的首个立场文件。SAGE在其2011年4月的会议上讨论了这类疫苗的使用建议。会议提呈的依据可以通过以下网址获取:http://www.who.int/immunization/sage/previous/en/index.html。
本文脚注仅提供有限的核心参考文献。本立场文件同时也提供了部分分级表的链接,利用这些分级表可以评估一些重要结论所需科学证据的质量。更全面的参考文献列表见《蜱传脑炎疫苗和接种背景文件》。2
背景
流行病学
在东欧、中欧和北欧国家以及在中国北部、蒙古和俄罗斯,蜱传脑炎病毒是中枢神经系统病毒感染的重要原因。蜱传脑炎地方性流行区覆盖欧亚大陆非热带森林带的南部,由法国东北部延伸至日本北海道。3每年报告的临床病例数约为10,000~12,000例,但这一数字应该远远偏低。即使在最严重的疫区,蜱传脑炎通常也仅局限于特定的森林疫点。一些国家(如德国)根据报告的临床病例数按区域确定高危地区。但是,对于蜱传脑炎,尚无规范的诊断标准,也没有高危地区的明确定义。
目前,临床病例报告发病率最高的是波罗的海国家、斯洛文尼亚和俄罗斯。例如,2009年,爱沙尼亚的全国发病率为10.40/10万,拉脱维亚为7.50/10万,立陶宛为6.89/10万,斯洛文尼亚为9.90/10万。42006年俄罗斯的平均发病率为2.44/10万,但在西伯利亚地区发病率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倍以上,其中有的地区甚至高出10倍。俄罗斯西北部报告的蜱传脑炎发病率也比较高。其他在其领土范围内有病例报告的或由于病毒在蜱中的高度流行而被认为是高危地区的国家还包括阿尔巴尼亚、奥地利、白俄罗斯、波斯尼亚、保加利亚、中国、克罗地亚、丹麦、芬兰、德国、希腊、匈牙利、意大利、蒙古、挪威、波兰、韩国、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瑞典、瑞士、土耳其和乌克兰。
在疫情最为严重的地区,男性比女性更常受到蜱传脑炎感染。尽管所有年龄组均可受染,但各地区病例的年龄分布不同。在西伯利亚西部的高流行区,虽然20%~30%的病例小于14岁,但20~49岁组人群发病率最高。5德国南部在1994~1998年期间共发病656例,其中12%(79例)为小于14岁儿童,42%(276例)为21~50岁人群,24%(157例)为60岁以上人群。6
气候、居住地以及休闲娱乐活动的变化正在改变着蜱传脑炎的流行病学。蜱传脑炎可能成为一个日渐严重的问题,因为过去认为的非流行区(例如,德国、立陶宛、斯堪的纳维亚的部分地区,俄罗斯和瑞士的一些区域)也有病例报告,并且呈地方性流行。2此外,流行区的海拔高度在明显扩大,最近奥地利和斯洛伐克的报道指出,流行区海拔已由800米以下扩至大约1500米以下范围。2
引起人类疾病的蜱传脑炎病毒有3种亚型:(1)欧洲亚型,流行于欧洲西部、北部、中部和东部地区;(2)远东亚型,流行于俄罗斯东部、中国和日本;(3)西伯利亚亚型,流行于俄罗斯所有地区(但主要是位于亚洲的地区)。7所有3个亚型都在波罗的海、俄罗斯位于欧洲的地区和西伯利亚共同传播。2
大部分病毒感染是由于在森林地区户外活动时遭蜱虫叮咬,但大约三分之一的确诊病例不能回忆起病前曾经接触过蜱虫。5蜱传脑炎发病的季节特征与蜱虫暴露增加的季节一致:即春季、夏季和秋季。8
欧洲亚型主要由蓖子硬蜱(Ixodesricinus)传播,远东和西伯利亚亚型主要由全沟硬蜱(Ixodespersulcatus)传播。不同时间、不同地点蜱虫感染病毒的比例差异很大;在奥地利和德国南部的流行区,1%~3%的蜱虫携带病毒,而在立陶宛、俄罗斯和瑞士的流行区,蜱虫的病毒感染率可高达10%~30%。但人群的发病率取决于很多因素,与本地蜱病毒感染率并不直接相关。3,9
幼虫、蛹和成虫蜱从病毒血症的动物(特别是小型啮齿类动物)吸血时可感染病毒,之后再次吸血时可感染包括人在内的脊椎动物。此外,蜱也可经卵或通过共同摄食感染病毒。
有100多种动物可感染病毒,其中一些可起到宿主的作用。偶尔感染病毒的牛,山羊或绵羊可通过未杀菌的奶或奶制品传播病毒,经消化道感染人类。10未见人传人的报道。
试图通过化学灭蜱来消除疾病的做法并不成功,穿杀虫剂浸泡过的服装或使用驱避剂最多也只是产生短暂的保护效果。但在流行地区室外活动时做好个人防护,可减少病毒暴露风险。个人防护措施包括:穿着适宜的衣服,每天检查皮肤是否受到蜱虫叮咬。对于居住在城市或非森林地区者以及不食用未经巴氏杀菌的奶制品的人员,其感染风险可以忽略不计。
病毒、发病机制和病原学诊断
蜱传脑炎病毒属于黄病毒科黄病毒属,包括约70种病毒,如登革热病毒、黄热病毒、流行性乙型脑炎病毒、西尼罗河病毒等。病毒颗粒由一个单链RNA分子组成,含核心膜和囊膜(E)蛋白。E蛋白区含血凝和中和相关抗原决定区,并可诱导宿主产生保护性免疫。3种蜱传脑炎病毒亚型((西部型、西伯利亚型和远东型)的基因和抗原密切相关,不易发生明显的抗原变异。11感染病毒的蜱叮咬人后,病毒首先在局部皮肤细胞复制,然后在局部淋巴结和网状内皮系统复制。病毒感染毛细血管内皮细胞后穿越血脑屏障。死亡病例有典型的神经病理学变化,包括脑脊髓灰质炎,尤以脊髓、脑干和小脑为明显。12
蜱传脑炎的病原学诊断需要实验室确认,因为临床表现相对不具有特异性。初期病毒血症阶段,可通过聚合酶链反应(PCR)检测病毒,也可移植到合适的细胞基或感染乳鼠进行病毒培养。在第二阶段,即神经病学阶段,个别病例可从其脑脊液或脑内检出病毒。出现神经系统症状时,通常可检出病毒抗体,血清学诊断可使用多种方法,如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中和抗体(NT)检测和血凝抑制(HI)技术。对于曾暴露于黄病毒的人员(包括接种过黄热病疫苗或流行性乙型脑炎疫苗的人员),在检测其病毒特异性免疫球蛋白G时,由于抗体交叉反应的存在,可能出现假阳性结果。此时需要采用高特异性的中和抗体检测确定其免疫力。13
疾病
蜱传脑炎的潜伏期为2~28天(常为7~14天),之后出现非特异性症状和体征,如疲乏、头痛和全身不适,持续1~8天,通常伴≥38℃的发热。再经过1~20天的无症状期,大约三分之一的临床病例会进入第二阶段,此时疾病通常表现为超过40℃的高热和中枢神经系统受累体征,如脑膜炎、脑炎(尤其是小脑共济失调)、脊髓炎或神经根炎。脑炎患者可出现昏迷和锥体束功能障碍,以及常累及肩部肌肉的瘫痪。不到40%的脑炎病例会遗留永久性中枢神经系统后遗症,包括各种神经精神疾病和认知障碍为特点的脑炎后综合征。5本病没有特异性治疗方法。
临床观察提示,疾病的严重程度和病毒亚型有关。远东亚型致病程度看来比欧洲亚型严重,西伯利亚亚型致病的严重性居中。远东亚型报告病死率为≥20%,西伯利亚亚型为6%~8%,欧洲亚型为1%~2%。7远东亚型可引起致命的出血热。个别慢性病例,其特点为病程进展缓慢,长达6个月以上,他们主要由西伯利亚亚型引起,发病者中也有儿童。4然而,各亚型之间的差异部分地与病人入选标准、医疗服务的可及性以及年龄别暴露等因素有关。
蜱传脑炎疫苗
首个蜱传脑炎疫苗于1937年在前苏联研发成功。当时,前苏联出现了蜱传脑炎暴发(时称俄罗斯春夏脑炎),构成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第一代疫苗源自鼠脑,有效但不良事件频发。现代的、反应原性低的疫苗采用细胞培养的福尔马林灭活病毒株。目前,有4种质量可靠、广泛使用的疫苗:FSME-Immun和Encepur分别在奥地利和德国生产,基于欧洲亚型病毒株;蜱传疫苗-莫斯科(TBE-MOSCOW)和EnceVir在俄罗斯生产,基于远东亚型株。还有一种中国生产的疫苗,在中国北部边境地区使用;不过,有关该疫苗的组分、安全性、效力和效果的详细文献尚未在国际期刊上发表。
虽然有很多观察性研究证明了这些疫苗的效果,但尚未开展随机对照试验来证实其效力。目前认为,针对此类疫苗开展随机对照试验是不符合伦理学原则的。
免疫原性评估可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中和抗体或血凝抑制方法。循环系统针对病毒的抗体达到或者高于当地认可水平(例如,中和抗体滴度≥10)时,通常被认为具有保护力。14然而,尚无系统的临床研究能够证实这种假设。此外,不同疫苗的免疫原性资料不能直接进行比较,因为生产商使用不同的检测方法,很少有独立的直接比较研究。
奥地利和德国的疫苗
市场上奥地利和德国产的蜱传脑炎疫苗分别为FSME-Immun(2001年后上市的新剂型)和Encepur-成人剂型。他们各自的儿童剂型分别是适用于1~15岁的FSME-Immun儿童剂型和适用于1~11岁儿童的Encepur-儿童剂型。FSME-Immun和Encepur最初分别于1976年和1994年获得注册许可。
FSME-Immun新剂型基于欧洲亚型的Neudörfl毒株,用人血清作为稳定剂。每剂抗原含量为2.4微克(成人剂型)和1.2微克(儿童剂型)。Encepur使用的是欧洲亚型的K23株,用蔗糖作为稳定剂。每剂抗原含量为1.5微克(成人剂型)和0.75微克(儿童剂型)。两种疫苗均遵循世卫组织的要求15生产。疫苗使用鸡胚成纤维细胞生产、甲醛灭活、氢氧化铝作佐剂。疫苗不含有聚明胶和硫柳汞,但终产品可能有微量甲醛(仅存于FSME-Immun)、庆大霉素、新霉素和氯四环素(仅存于Encepur)。2~8℃储存时,两种疫苗效期为30个月。疫苗使用预充式注射器,肌内注射,每剂0.5毫升(成人)和0.25毫升(儿童)。
根据生产商要求,FSME-Immun和Encepur基础免疫都需要3剂。常规的免疫程序中,前2剂之间需间隔1~3个月,第2、3剂间隔5~12个月(Encepur要求9~12个月)。若采用快速接种程序,FSME-Immun接种程序为0和14天接种前2剂,5~12个月后接种第三剂;Encepur前2剂在0和14天接种,9~12个月后接种第三剂。此外,Encepur可用加急程序,在0、7和21天各接种1剂,在12~18个月后接种第4剂。两种疫苗生产商均建议完成基础免疫3年后加强接种1剂,以后每隔5年加强1剂,50岁以后加强免疫时间间隔为3年,奥地利还建议60岁以上者每3年加强1剂。
为确定Encepur-成人剂型和Encepur-儿童剂型的最佳程序,两项随机对照研究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和中和抗体法,比较了4种不同的免疫程序引起的免疫反应。其中一项研究16纳入了398名12岁及以上的研究对象,另一项研究17纳入了294名1~11岁儿童。这两项研究均得出以下结论:在0、7和21天接种疫苗的加急免疫程序,就其快速诱导的免疫反应和稳定的中和抗体滴度持续超过300天来看,要优于其他3种程序(即接种于0、28和300天;0、21和300天;以及0、14和300天)。对FSME-Immun尚未开展类似的研究。
疫苗的免疫原性和有效性
关于Encepur和FSME-Immun基础免疫的免疫原性,已经有一些研究发表18,19,20,21。最近Cochrane中心的一篇综述22总结了目前上市的蜱传脑炎疫苗(Encepur-儿童剂型、Encepur疫苗成人剂型和FSME-Immun新剂型)的11项试验(包括4项随机对照试验)血清转化资料。共计有5063名儿童和成人参加这4个试验,92%~100%的研究对象有酶联免疫吸附试验、血凝抑制或中和抗体法测定的血清转化资料。常规免疫程序(0,28和300天)和加急程序(0,7和21天)后可获得同样高的免疫原性。其后对334名儿童开展的一项随机对照试验发现,95%以上研究对象在接种2剂Encepur-儿童剂型或FSME-Immun儿童剂型后中和滴度达到10及以上18。
几乎没有资料说明接种间隔远远超过推荐间隔时疫苗的免疫原性和效果如何。有一项研究专门探讨了未按疫苗生产商推荐程序接种后人体免疫记忆的持久性23;结果发现,大多数研究对象可通过对蜱传脑炎抗原的回忆性抗体反应,启动免疫应答。无论他们最后一剂次接种疫苗已经过去了多长时间(该研究中为≤20年),即使是那些之前只接种过一次的人,甚至对于接种加强剂次前血清反应呈阴性的人,他们体内都留存有免疫记忆。这些发现表明,前2剂或前3剂之间的间隔不是后续免疫接种成功与否的关键参数。另一方面,初免可能不足以产生对疾病的保护作用24。
受种者中发生“免疫保护突破病例”非常罕见,但确有发生,特别是在老年人中。例如,奥地利2002年~2008年报告“免疫保护突破病例”25例,其中8例是按照生产商建议的免疫程序完成疫苗接种的;瑞典2000年~2008年发病27例25,其中21例已经按照适宜的程序接种了2剂及以上疫苗。
奥地利1994年~2001年的疫苗现场效果研究发现,2剂FSME-Immun疫苗对临床疾病的保护率为96.4%~100%,3剂的保护率为96%~98.7%26。2000年~2006年类似的研究发现,按照建议的免疫程序接种3剂及以上疫苗的总效果(主要是FSME-Immun)约为99%27。奥地利使用现有疫苗的经验表明,高接种率可以使蜱传脑炎发病率明显下降。
免疫保护的持久性和接种加强免疫剂次的必要性
纵向研究显示,基础免疫后,中和抗体几何平均滴度在第一年下降,之后趋于平稳。长期观察研究表明,基础免疫后加强接种1剂及以上的情况下,免疫力持续时间比以前预期的5年还要长。比较分析研究表明,给予1剂及以上加强免疫后,抗体持久性可能会长于仅完成基础免疫者18,28,29,30,31,32,33。不管年龄如何,抗体下降的速度相似;但与年轻人比,50至60岁及以上年龄人群血清抗体更容易呈阴性,因为他们接种加强剂次后体内产生的抗体滴度较低28,29,30,31,34,35。
奥地利的数据表明,对于90%以上的接种者而言,加强剂次诱导的保护性抗体可维持6年以上,而对于偶有发生的“免疫保护突破病例”,其发病与距离最后一次免疫之间的时间长短并无关系28。之后来自奥地利的数据表明,90%以上的受种者自最后一剂加强接种后,抗体滴度可维持8年及以上。目前还没有类似的针对基础免疫的数据,但也无证据表明抗体滴度会明显下降。保护性抗体滴度的阈值至今尚未正式确定。
由于延长加强剂次和基础免疫之间的间隔会降低成本和提高接受度,一些国家正在修订加强剂次的接种建议。目前,只有瑞士建议基础免疫和首次加强免疫之间,以及后续加强免疫之间的间隔为10年36。
Encepur和FSME–Immun的安全性
由Encepur和FSME-Immun 2001年以前的配方引发的疫苗不良事件比较频繁。目前的配方在安全性方面有了很大改进,因此被认为是安全的37。
上面提到的Cochrane综述22总结了4项随机对照试验对Encepur-儿童剂型、Encepur-成人剂型和FSME-Immun新配方,在安全性方面进行研究后得到的数据。试验共包括5063名儿童和成人。虽然不良事件常有报告(45%及以下的接种者注射部位有短暂发红和疼痛,38℃及以上发热的接种者比例为5%~6%及以下),但都不严重或并不危及生命。一项随机对照单盲多中心试验,纳入334名1~11岁儿童,结果发现,受种者对FSME-Immun儿童剂型和Encepur-儿童剂型的耐受性良好,两者安全性类似;没有与疫苗相关的严重不良事件报告18。另一项类似的单盲多中心随机对照III期临床研究比较了疫苗在303名1~11岁儿童中的免疫原性和安全性,结果发现受种者的全身反应发生率均很低,且两种疫苗结果类似21。
在18~67岁的成人中对加强疫苗剂次后的不良事件进行了调查,研究对象的基础免疫是接种了2剂FSME-Immun或Encepur-成人剂型、第3剂接种FSME-Immun。当他们3年后接种加强剂次时,与加强接种相关的不良事件多不常见且为轻度31。另一项研究发现,在首次加强免疫三年后,再次用Encepur进行加强剂次接种时,全部受种者都表现出良好的耐受性38。
上市后研究确认了这些疫苗接种后没有严重不良事件发生。因此,2002年一份独立的上市后哨点监测研究报告指出,接种25905剂Encepur和FSME-Immun的不良事件发生率为0.41%,最常见的不良反应是轻度至中度发热(低于40℃)、注射部位局部反应和疼痛。同样,对疫苗销售量超过500万剂的上市后监测也没有发现任何潜在的安全性风险。没有报告提示奥地利或德国的蜱传脑炎疫苗在与其他疫苗同时使用时(例如为旅行者接种时)会降低免疫原性或安全性。
俄罗斯疫苗
有两种蜱传脑炎疫苗在俄罗斯生产。其中,TBE-Moscow疫苗于1982年被批准用于成年人;在1999年,经过进一步的改进纯化工艺,它被批准用于3岁及以上儿童。自1982年以来,俄罗斯及其邻国已有超过2500万人接种了该疫苗。另一种是EnceVir,它于2001年在俄罗斯获得上市许可,也获准用于3岁及以上儿童39。
TBE-Moscow疫苗基于远东亚型的Sofjin株。病毒在鼠脑传代后,进一步在原代鸡胚细胞增殖,然后用福尔马林灭活、过滤、浓缩并用硫酸鱼精蛋白赋形处理,再添加人血白蛋白(500微克/剂)作稳定剂、添加明胶和蔗糖,最后冻干。疫苗病毒蛋白的浓度为0.50~0.75微克/剂,其免疫原性被调整到预设的标准。使用前,用含有氢氧化铝佐剂的液体溶解冻干疫苗。
EnceVir使用的是远东亚型205株,其制作步骤几乎与TBE-Moscow疫苗完全相同。疫苗病毒蛋白的浓度为1.5~2.5微克/剂,用氢氧化铝作佐剂、人血清白蛋白(250μg/剂)作稳定剂,但不冻干。生产过程中使用卡那霉素。终产品可残留痕量硫酸鱼精蛋白。
两种疫苗都符合世卫组织的疫苗生产要求,并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控制39。在8℃储存时,EnceVir的保质期为2年,TBE-Moscow疫苗的保质期为3年。两种疫苗在9~25℃可保持2天的稳定性。
俄罗斯的这两种疫苗未获准用于3岁以下儿童。3岁及以上人群接种剂量为0.5毫升,肌内注射。TBE-Moscow疫苗生产商建议的标准基础免疫程序为2剂,间隔1~7个月;Ence-Vir疫苗生产商建议接种2剂,间隔5~7个月。EnceVir在紧急情况下可以使用快速程序:前2剂之间接种间隔1~2个月。两种疫苗均需要在第2剂基础免疫后12个月加强免疫1剂次,以后则每3年1剂次。
疫苗免疫原性和有效性
在7~17岁儿童中,采用血凝抑制方法检测,对TBE-Moscow疫苗和FSME-Immun的免疫原性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第二剂接种四周后,接种TBE-Moscow疫苗和FSME-Immun的人员中分别有91.5%和98.7%出现血清阳转。2001年~2002年对TBE-Moscow疫苗和EnceVir疫苗的免疫原性进行了比较研究40。研究人员用血凝抑制方法对200名成人接种2剂TBE-Moscow或EnceVir疫苗后的免疫应答进行了评价。其中,一半受种者两剂接种间隔为2个月,另一半受种者两剂接种间隔5个月。结果发现,对于TBE-Moscow疫苗受种者,当其两剂间隔为2个月时,有84%的人抗体滴度达到或超过1:80;当其两剂间隔为5个月时,该比例为93%。对于EnceVir疫苗受种者,相应的结果分别为82%和89%。
2003年,俄罗斯国家药品监督管理机构在325名儿童和青少年中,对TBE-Moscow和EnceVir疫苗进行了比较研究41。研究对象分为3个年龄组(分别是3~6岁、7~14岁和15~18岁)。间隔2个月接种2剂疫苗后,3~6岁组TBE-Moscow疫苗受种者中96%的出现血凝抑制抗体滴度4倍及以上增长,相应的7~14岁组为93%、15~18岁组为89%。而接种EnceVir疫苗的各年龄组对应结果分别为84%、97%和92%(由于样本量小,无法计算可信区间)。
最近的一项研究纳入290名成人,比较了TBE-Moscow、EnceVir、FSME–Immun新配方和Encepur-成人剂型疫苗的免疫原性42。该研究衡量了接种3剂疫苗后2~5个月和2年的免疫原性。所有疫苗都诱导出抗远东亚型P-73株的抗体。TBE-Moscow疫苗接种后2~5个月抗体阳转率为100%,2年后为94%。EnceVir疫苗分别为88%和84%;FSME-Immun疫苗分别为88.2%和78.1%;Encepur-成人剂型疫苗为100%和100%(由于样本量小,无法计算可信区间)。
1996年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地区开始了群众性免疫规划,结果表明,俄罗斯生产的疫苗非常有效。到2005年,已有270万人接种了3剂疫苗,大多数接种的是TBE-Moscow疫苗43。接种率由项目开始的35%增加至2000年的55%,到2006年达到72%。该地区蜱传脑炎的发病率由1996年的42.1/10万下降到2000年的9.7/10万、2006年的5.1/10万。各年龄组发病均有下降。比较接种和未接种人群的发病情况,结果提示该疫苗的效果由2000年的62%增加至2006年的89%。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增长可能也是由于采取了更严格的诊断标准43。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地区对儿童开展了该疫苗的常规免疫,蜱传脑炎的发病率由1999年的48.5/10万下降到2003年的6.1/10万。
对EnceVir疫苗3剂基础免疫接种的广泛监测表明,高滴度抗体至少可持续3年44。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地区2006年,完成全程免疫的人中发生“免疫保护突破病例”的发病率为1.5/10万(未接种疫苗人群的发病率为13.0/10万)。该地区自1996年项目开始,使用的疫苗有俄罗斯生产的疫苗和奥地利、德国生产的疫苗,但大约80%是TBE-Moscow疫苗43。目前尚没有关于老人接种俄罗斯疫苗诱导的免疫力及其持久性的数据。
TBE–Moscow和EnceVir疫苗的安全性
尚无有关这些疫苗安全性的大规模随机对照试验结果发表。对疫苗引起的全身和局部不良反应的小规模研究表明,俄罗斯疫苗反应原性中等,2种疫苗之间无显著差异。2002年~2003年,塔拉谢维奇(Tarasevich)国家医学生物制品检定和标准化研究院开展了一项研究,评估TBE-Moscow和EnceVir疫苗在325名儿童和400名成人中引发的局部和全身反应原性,结果未见严重不良事件41。两种疫苗的反应原性中等,并且两者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关于TBE-Moscow疫苗的安全性,其他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此外,上市后监测未发现EnceVir疫苗的任何严重不良事件。
然而,在2010年和2011年,某些批次的EnceVir疫苗接种后出现多例高热(发生率不超过19%)和过敏反应,尤其是在儿童中。这些批次的疫苗后被生产商召回,经过持续的评估,不建议将EnceVir疫苗用于3~17岁儿童45。抗原含量为成人剂型的一半的儿科剂型目前正在研发中。
没有证据表明俄罗斯生产的疫苗与其他疫苗同时接种时(例如为旅行者接种时),其免疫原性和安全性会受到影响,但这方面独立发表的文献有限。
现有疫苗的交叉保护
目前有限的临床证据表明,奥地利和德国生产的两种疫苗不仅可诱导同亚型的保护性免疫力,对远东和西伯利亚亚型也能产生免疫力。可能是因为这些亚型的基因和抗原之间有相似性,而产生交叉保护,这在某些非临床研究中可以获得相应的证据。46成人接种Encepur疫苗可诱导高滴度的抗体,可中和西方亚型和远东亚型42,46。同样,所有4种疫苗均可诱导中和远东亚型的抗体47。此外,最近一项研究使用接种FSME-Immun疫苗后的血清样本,发现中和欧洲、远东和西伯利亚亚型的中和抗体滴度完全相同48。临床前研究也支持疫苗有交叉保护性免疫,研究发现小鼠接种欧洲亚型疫苗后,可抵抗多种东方病毒分离物的致命攻击。
一些研究表明,现有疫苗可以互换使用。
禁忌症及注意事项
虽然目前注册的疫苗是使用鸡胚细胞生产的,但对鸡蛋蛋白轻度过敏并非禁忌症。
正在接受免疫抑制治疗者接种蜱传脑炎疫苗后,疫苗诱导的保护性免疫可显著降低。此时,应采用血清学方法评估抗体应答;如有必要,需要额外接种疫苗。一般情况下,如果发热高于38.5℃或患有其他严重疾病,应推迟接种。生活在蜱传脑炎高发(5/10万以上)地区的孕妇应接种疫苗。对居住在蜱传脑炎发病率为中度或低度(低于5/10万)地区者,应综合考虑接种的利弊(例如,卫生专业人员应评估孕妇是否会参加那些导致患病风险升高的户外活动)。
已暴露于其他黄病毒者可产生交叉反应抗体,可能会干扰接种蜱传脑炎疫苗后的血清学反应12,13;同时,如体内之前存在蜱传脑炎病毒抗体,则可干扰乙脑疫苗的抗体反应49。
暴露后预防
一般认为,在蜱叮咬后再去接种疫苗,已经来不及在(可能)发病前诱导免疫,并且理论上存在抗体依赖性感染增强的风险。因此,对未接种疫苗者在遭遇蜱叮咬后,不建议进行暴露后预防。
在西欧发现,暴露后注射含高浓度蜱传脑炎病毒抗体的免疫球蛋白没有保护作用,因此也不再推荐此方法。然而,最近一项关于俄罗斯使用免疫球蛋白经验的综述表明,暴露后早期接种俄罗斯生产的免疫球蛋白有一定保护作用。
疫苗接种的成本效果
在蜱传脑炎流行区,无论对于个人还是社会,疾病的代价高昂,特别是本病经常会有长久的神经系统后遗症。奥地利通过1991~2000年间开展的免疫接种活动,降低了照护病人的费用、减少了生产力损失和提前退休,估计挽回了8000万美元的损失50。近期没有关于蜱传脑炎疫苗接种的成本效果分析的文献发表。但通常认为,疫苗价格和目标人群的界定对疫苗成本效果的影响甚大。
世卫组织关于蜱传脑炎疫苗使用的政策
免疫接种对蜱传脑炎可提供最有效的保护51。世卫组织认为,奥地利和德国生产的疫苗对1岁及以上人群安全而有效。俄罗斯联邦生产的疫苗对3岁及以上人群安全而有效,尽管其支持性数据较有限52。现有疫苗基本上能够抵御亚洲和欧洲地区传播的所有病毒亚型53。
由于各地蜱传脑炎的发病率可能有很大差异,甚至在同一地理区域也是如此,公共免疫接种策略应基于在国家、区域或地区层面开展的风险评估而确定,而且要适合于当地的流行情况。因此,在确定将要采用的最适宜的预防措施前,必须建立病例报告体系。同样,卫生主管部门对免疫接种规划进行决策时,也应通过成本效果分析获取信息。
在疾病高地方性流行地区(即,免疫接种前每年平均临床疾病发病率≥5/10万),个体感染风险高,世卫组织建议对该地区所有年龄组人群(包括儿童)接种疫苗。应根据流行病学情况,考虑是否将蜱传脑炎疫苗纳入国家或区域的免疫规划。
由于本病在50~60岁以上人群中发病往往更严重,这一年龄组是免疫接种的重点目标人群。
免疫接种前发病率中度或低度的地区(即,5年期间年平均发病率低于5/10万),或疾病仅限于特定地理区域或某些户外活动,免疫接种应针对最易患病的群体。
由非流行区前往流行区的旅行者,如果有大量户外活动,也应给予免疫接种。
蜱传脑炎疫苗的基础免疫需要3剂。有持续感染风险者应至少接种1次加强剂次54。各剂次间可接受的时间间隔范围相当大,各国主管部门应在此范围内选择适用于国家、区域或地区免疫规划的最合理的基础免疫程序。
奥地利和德国生产的疫苗,第一、二剂次间可间隔1~3个月,第2剂和第3剂之间间隔5~12个月。若需要快速产生保护,例如为前往地方性流行区的人员接种时,前2剂间隔可缩短为1~2周。
目前有关完成3剂基础免疫后的保护期限、是否需要加强剂次以及加强剂次间的最佳间隔等信息甚少。虽然有明确的迹象表明加强剂次的时间间隔可以远远超过生产厂商建议的间隔,但现有证据仍不足以对加强剂次的次数和最佳频率提出确定的建议54。因此,在有更可靠的信息可用之前,各国应继续根据当地流行病学和目前的程序提出疫苗使用的建议。
通常对50岁以下的健康人,建议其加强剂次间隔时间为3~5年;不过,在一些蜱传脑炎呈地方性流行的地区(如瑞士),目前建议不超过10年。
由于本病在50岁至60岁及以上的人群中,病情往往更严重,且引起的免疫应答较弱,为慎重起见,在获得更多明确的信息之前,建议此年龄组人群加强剂次的间隔时间为3~5年53。
对于俄罗斯联邦生产的疫苗,建议前2剂间隔时间为1~7个月,2、3剂间隔12个月。建议对有持续暴露风险者每3年加强1剂。在获得更多有关保护期的数据之前,应维持目前建议的加强剂次间隔时间。
不管延误时间有多久,中断的免疫程序都应继续进行,无须重复以前的剂次。
虽然没有证据提示现有的蜱传脑炎疫苗和同时接种的其它疫苗之间会有任何干扰,但应开展相应的研究阐明潜在的免疫交互作用。另外,还需要研究之前接种过黄热病疫苗或乙脑疫苗者在接种蜱传脑炎疫苗后的免疫反应。
不建议在蜱叮咬后进行暴露后接种。西欧国家也不推荐在暴露后接种特异性免疫球蛋白进行被动暴露后预防,但在俄罗斯联邦时有使用。
大量的知识空白成为目前制定更具体的蜱传脑炎防控指南的障碍。尤其是需要开展更多的研究来评估接种加强免疫剂次的必要性及时间安排。鼓励各国对不同疫苗接种方案的有效性及成本效果进行评估。
蜱传脑炎的监测对于了解其流行病学特征、估量疾病负担、发现高危地区和疾病新发地区以及证明控制措施的效果至关重要。需要对临床病例的定义、病例报告要求以及随访流程(确定蜱传脑炎导致的长期后遗症情况)进行标准化。同样,也需要标准化的试剂,以便比较不同实验室的检测结果。
在蜱传脑炎地方性流行区,应使人们可以方便地通过各种渠道(如学校、医师诊所和旅游信息传单)获悉蜱传脑炎的疾病知识、传播媒介和传播方式以及可采用的预防措施。
参考文献
1 如欲获取更多信息, 请访问 http://www.who.int/immunization/sage/en/.
2 Kollaritsch H etal. Background document on vaccines and vaccination against tick–borne encephalitis. Geneva, WHO Strategic Advisory Group of Experts on Immunization, 2011 (http://www.
who.int/immunization/sage/6_TBE_backgr_ 18_Mar_net_ apr_2011.pdf, 访问日期:2011 年 5 月).
3 Süss J. Tick–borne encephalitis in Europe and beyond––the epidemiological situation as of 2007.
EuroSurveillance, 2008,13(26):pii =18916 (http://www.eurosurveillance.org/viewarticle.aspx?articleId=18916, 访 问日期: 2011 年 5 月).
4 Stefanoff P etal. Reliable surveillance of tick–borne encephalitis in European countries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vaccine recommendations. Vaccine, 2011, 29:1283–1288.
5 Poponnikova TV. Specific clinical and epidemiological features of tick–borne encephalitis in Western Siber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dical Microbiology, 2006, 296(Suppl. 40):S59–S62.
6 Kaiser R. Tick–borne encephalitis. Infectious Disease Clinics of North America, 2008, 22:561–575.
7 Fauquet CM etal, eds. Virus taxonomy: VIIIth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n Taxonomy of Viruses. San Diego, CA, Elsevier Academic Press, 2005: 986
8 Gritsun TS et al. Tick–borne encephalitis. Antiviral Research, 2003, 57:129–146.
9 Süss J et al. TBE incidence versus virus prevalence and increased prevalence of the TBE virus in Ixodes ricinus removed from huma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dical Microbiology, 2006, 296(Suppl. 40):S63–S68.
10 Holzmann H etal. Tick-borne encephalitis from eating goat cheese in a mountain region of Austria.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2009, 15:1671–1673.
11 Ecker M etal. Sequence analysis and genetic classification of tick–borne encephalitis viruses from Europe and Asia. Journal of General Virology, 1999, 80:179–185.
12 Gelpi E. Inflammatory response in human tick–borne encephalitis: analysis of postmortem brain tissue. Journal of Neurovirology, 2006, 12:322–327.
13 Sonnenberg K et al. State-of-the-art serological techniques for detection of antibodies against tick–borne encephalitis viru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dical Micro- biology, 2004, 293(Suppl. 37):S148–S151.
14 Holzmann H etal. Correlation between ELISA, hemagglutination inhibition, and neutralization tests after vaccination against tick–borne encephalitis. Journal of Medical Virology, 1996, 48:102–107.
15 Requirements for tick-borne encephalitis vaccine (inactivated) [Annex 2] .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1997, WHO technical report series 889. (http://whqlibdoc.who.int/trs/WHO_TRS_889.pdf; 访问日期: 2011 年 5 月)
16 Schondorf Iet al. Tick–borne encephalitis (TBE) vaccination: applying the most suitable vaccination schedule. Vaccine, 2007, 25:1470–1476.
17 Schoendorf Iet al. Tick–borne encephalitis (TBE) vaccination in children: advantage of the rapid immunization schedule (i.e., days 0, 7, 21). Human Vaccines, 2007, 2:42–47.
18 Wittermann C et al. Antibody response following administration of two tick–borne encephalitis vaccines using two different vaccination schedules. Vaccine, 2009, 27:1661–1666.
19 Ehrlich HJ et al. Randomised, phase II dose finding studies of a modifi ed tick–borne encephalitis vaccine. Vaccine, 2006, 24:5256–5263.
20 Loew–Baselli LA et al. Safety and immunogenicity of the modified adult tick–borne encephalitis vaccine. Vaccine, 2006, 24:5256–5263.
21 Poellabauer E.M et al. Comparison of immunogenicity and safety between two paediatric TBE vaccines. Vaccine, 2010, 28:4680–4685.
22 Demicheli V etal. Vaccines for preventing tick–borne encephalitis. Cochrane Database of Systematic Reviews, 2009, (1):CD000977.
23 Schosser R et al. Seropositivity before and seroprotection after a booster vaccination with FSME–IMMUN® adults in subjects with a time interval of >4,5 years since the last TBE vaccination. Résumé présenté lors du 10ème Symposium international de Jena sur les maladies transmises par les tiques (précédemment appelé IPS), Weimar, Allemagne, 19-21 mars 2011.
24 Stiasny K et al. Characteristics of antibody responses in tick–borne encephalitis vaccination breakthroughs. Vaccine, 2009, 27:7021–7026.
25 Andersson CR et al. Vaccine failures after active immunisation against tick–borne encephalitis. Vaccine, 2010, 28:2827–2831.
26 Kunz C. TBE vaccination and the Austrian experience. Vaccine, 2003, 21(Suppl. 1): S50–S55.
27 Heinz FX et al. Field effectiveness of vaccination against tick–borne encephalitis. Vaccine, 2007, 25:7559–7567.
28 Paulke–Korinek M et al. Booster vaccinations against tick–borne encephalitis: 6 years follow–up indicates
9(o)R(ng)e–n(t)d(e)i(r)m–Wa(pr)g(o)n(te)e(c)r(t)iP(o)n.et(V)a(a)l(c)ciA(n)n(e),tibody(2009), p(27)e:rsistence(7027–70) fo(30).llowing booster vaccination against tick–borne encephalitis:
3-year post-booster follow-up, Vaccine, 2007, 25:5097–5101.
30 Rendi–Wagner P et al. Persistence of protective immunity following vaccination against tick–borne encephalitis–longer than expected? Vaccine, 2004, 22:2743–2749.
31 Rendi–Wagner P et al. Persistence of antibodies after vaccination against tick–borne encephalit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dical Microbiology, 2006, 296 (Suppl. 40):S202–S207.
32 Loew–Baselli A et al. Seropersistence of tick–borne encephalitis antibodies, safety and booster response to FSME–IMMUN® 0.5 ml in adults aged 18–67 years. Human Vaccines, 2009, 5: 551–556.
33 Plentz A et al. Long–term persistence of tick–borne encephalitis antibodies in adults 5 years after booster vaccination with Encepur Adults. Vaccine, 2009,27:853–856.
34 Hainz U et al. Insufficient protection for healthy elderly adults by tetanus and TBE vaccines. Vaccine, 2005, 23:3232–3235.
35 Weinberger B et al. Decreased antibody titers and booster responses in tick–borne encephalitis vaccinees aged
50–90 years. Vaccine, 2010, 28:3511–3515.
36 [Recommendations on immunization against tick-borne encephalitis]. Bulletin des Bundesamt für Gesundheit (Schweiz), 2006, 13:225–231 [仅有德文版] .
37 Zent O et al. Kinetics of the immune response after primary and booster immunization against tick–borne encephalitis (TBE) in adults using the rapid immunization schedule. Vaccine, 2003, 21:4655–4660.
38 Beran J et al. Long–term immunity after vaccination against tick–borne encephalitis with Encepur using the rapid vaccination schedul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dical Microbiology, 2004, 293 (Suppl. 37):S130–S133.
39 Vorob’eva MS et al. [Vaccines, immunoglobulins, and test systems for the prevention and diagnosis of tick–borne encephalitis]. Voprosy Virusologii, 2007, 52:30–36 [仅有俄文版] .
40 Gorbunov MA et al. Results of clinical evaluation of EnceVir vaccine against tick–borne encephalitis. Epidemiology and Vaccinoprophylaxis, 2002, 5:49 [仅有俄文版] .
41 Pavlova BG et al .[Immunization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withinactivated vaccines against tick–borne encephalitis]. Biopreparations, 2003, 1:24–28 [俄文版] .
42 Leonova GN etal. Evaluation of vaccine Encepur-Adult for induction of human neutralizing antibodies against recent Far Eastern subtype strains of tick–borne encephalitis virus. Vaccine, 2007, 25:895–901.
43 Romanenko VV etal. [Experience in implementing the mass immunization program against tick–borne encephalitis in the Sverdlovsk Region]. Voprosy Virusologii, 2007, 6: 22–25 [仅有俄文版] .
44 Il’ichenko TE et al. [Organization of Public Health], Siberian Journal of Medicine, 2009, 2:50–55 [仅有俄文版].
45 可访问 http://www.roszdravnadzor.ru/i/upload/files/1304670552.66323-5245.pdf
46 Klockmann U etal. Protection against European isolates of tick–borne encephalitis virus after vaccination with a new tick–borne encephalitis vaccine. Vaccine, 1991, 9: 210–212.
47 Leonova GN etal. Characterization of neutralizing antibodies to Far Eastern of tick–borne encephalitis virus subtype and the antibody avidity for four tick–borne encephalitis vaccines in human. Vaccine, 2009,
27:2899–2904.
48 Orlinger KK etal. A tick–borne encephalitis vaccine based on the European prototypestrain induces broadly reactive cross-neutralizing antibodies in humans. Jour 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2011, 203:1556–1564.
49 Schuller E et al. Effect of pre-existing anti-tick-borne encephalitis virus immunity on neutralising antibody
response to the Vero cell derived, inactivated Japanese encephalitis virus vaccine candidate IC51. Vaccine, 2008, 26:6151–6156.
50 Schwarz B. [Health economics of early summer meningoencephalitis in Austria. Effects of a vaccination campaign 1981 to 1990]. Wiener Medizinische Wochenschrift, 1993, 143:551–555 [仅有德文版] .
51 Grading of scientific evidence – Table I (vaccine efficacy and effectiveness). 可访问 http://www.who.int/entity/immunization/TBE_grad_efficacy.pdf
52 Grading of scientific evidence – Table II (vaccine safety). 可访问 http://www.who.int/entity/immunization/TBE_grad_safety.pdf
53 Grading of scientific evidence – Table III (induction of cross-protection). 可访问 http://www.who.int/entity/immunization/TBE_grad_crossprotection.pdf
54 Grading of scientific evidence – TablesIVa and IVb (duration of protection after primary immunization only and after primary immunizations plus one booster dose). 可访问
http://www.who.int/entity/immunization/TBE_duration_protection.pdf
(Weekly Epidemiological Record. No.24, 2011, 86, pp. 241-256)
Vaccines against tick-borne encephalitis: WHO position paper – 2011
Hits: 43
- 生物类似药药学相似性研究的问题与解答(征求意见稿)
- 麻疹疫苗:世卫组织的立场文件
- 已上市境外生产药品转移至境内生产的药品上市注册申请申报资料要求(预防用生物制品)
- 生物技术/生物制品在生产工艺变更前后的可比性
- 疫苗生产场地变更质量可比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 已上市疫苗药学变更研究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
- 已上市生物制品药学变更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试行)
- 青少年免疫接种讨论指南
- 推荐的儿童和青少年免疫计划:美国,2025年:政策声明
- 儿童免疫接种讨论指南
- 建议用于出生至 6 岁儿童疫苗接种计划
- 脑膜炎(细菌性)和脑膜炎球菌病:识别、诊断和管理NICE指南更新摘要
- 轮状病毒疫苗:世卫组织立场文件-2021年7月
- 关于新冠肺炎疫苗抗原成分的声明 2024年12月
- 多糖结合疫苗药学研究及评价技术指导原则(试行)
- 疫苗临床试验统计学指导原则(试行)
- ACIP建议
- 药物临床试验样本量估计指导原则(试行)
- 预防用猴痘疫苗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试行)
- 美国胃肠病学会免疫抑制药物治疗期间乙型肝炎病毒再激活的预防和治疗指南
- 免疫抑制情况下的乙型肝炎再激活
- 使用自体配子降低生育治疗期间病毒传播风险的建议:委员会意见
- HBV筛查、检测和诊断
- 选择初始 HBV 治疗方案
- 何时开始HBV治疗
- 监测开始接受丙肝治疗、正在接受治疗或已经完成治疗的患者
- 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的初步评估
- 疫苗说明书临床相关信息撰写指导原则(试行)
- 预防用猴痘疫苗药学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试行)
- 了解疫苗接种率的行为和社会驱动因素 世卫组织立场文件 – 2022年5月
- 2025年至2026年夏季新冠肺炎疫苗使用指南
- COVID-19 体征、症状和疾病严重程度:临床医生指南
- 预防和控制儿童流感的建议,2024–2025:政策声明
- 预防和控制儿童流感的建议,2024–2025:技术报告
- 卡介苗疫苗:世卫组织立场文件——2018年2月
- 减轻疫苗接种疼痛:世界卫生组织(WHO)立场文件—2015年9月
- 霍乱疫苗:世卫组织立场文件 – 2017 年 8 月
- 维生素A用于美国麻疹管理
- 生物制品注册受理审查指南(试行)
- 登革热疫苗:世卫组织立场文件 – 2024 年 5 月
- 白喉疫苗:世卫组织立场文件——2017年8月
- 世卫组织关于甲型肝炎疫苗的立场文件 – 2022年10月
- 世界卫生组织《根除特定类型脊髓灰质炎后遏制脊髓灰质炎病毒指南》 — 全球,2015 年
- 老年人 RSV 疫苗指南
- 英国2025年常规免疫计划
- 麻疹、腮腺炎、风疹疫苗 (PRIORIX):免疫实践咨询委员会的建议 — 美国,2022 年
- 2025 年推荐的7至18岁儿童和青少年免疫接种计划
- 乙型肝炎疫苗:世界卫生组织立场文件(2017 年 7 月)
- 全科医生带状疱疹疫苗接种计划技术指南
- AGA 关于预防和治疗高危人群乙型肝炎病毒再激活的临床实践指南
- 世界卫生组织关于戊型肝炎疫苗的立场文件(2015 年5 月)
- 世界卫生组织立场文件:b 型流感嗜血杆菌疫苗的接种(2013 年 7 月)
- 人乳头状瘤病毒疫苗:世卫组织立场文件(2022年更新)
- 2022年美国动物医院协会(AAHA)推荐的犬类疫苗指南
- 流感疫苗:世卫组织立场文件—— 2022年5月
- 日本脑炎疫苗:WHO 立场文件
- 猴痘临床指南
- 疟疾疫苗:世卫组织的立场文件
- 麻疹疫苗:世卫组织立场文件—2017年4月
- 脑膜炎球菌疫苗:世卫组织关于非洲脑膜炎地带国家使用多价脑膜炎球菌结合疫苗的立场文件,2024 年 1 月
- A 群脑膜炎球菌结合疫苗:更新后的指导意见(2015 年 2 月)
- 百日咳疫苗:世卫组织立场文件 – 2015 年 8 月
- 猴痘的临床管理与感染预防与控制 临时快速响应指南
- 老年人肺炎球菌疫苗接种考虑因素
- 肺炎球菌疫苗:世卫组织关于其在社区爆发环境中使用的立场文件
- 婴幼儿使用的肺炎球菌结合疫苗:世卫组织立场文件——2019年2月
- 脊灰疫苗:世卫组织立场文件 – 2022年6月
- 风疹疫苗:世卫组织立场文件——2020年7月
- 世界卫生组织关于破伤风疫苗的立场文件——2017 年 2 月
- 蜱传脑炎疫苗: 世卫组织立场文件 – 2011 年
- 伤寒疫苗:世卫组织立场文件 – 2018 年 3 月
- 水痘疫苗和带状疱疹疫苗: 世界卫生组织立场文件(2014年6月)
- LC16m8(冻干牛痘减毒活疫苗)天花和 mpox 疫苗:临时指南,2025 年 4 月 22 日
- 世卫组织关于黄热病疫苗的立场文件(2013 年 6 月)
- 黄热病疫苗:世卫组织对分次剂量使用的立场 – 2017 年 6 月
- 世卫组织关于免疫接种以保护婴儿感染呼吸道合胞病毒病的立场文件 2025 年 5 月
- 世卫组织接触者追踪指南
- 世卫组织关于带状疱疹疫苗的立场文件 – 2025 年 7 月
- 世卫组织立场文件:5岁以下婴幼儿肺炎球菌结合疫苗——2025年9月
- 世界卫生组织关于水痘疫苗的立场文件 ——2025 年 11 月
- 减轻疫苗接种时的疼痛:世界卫生组织立场文件 ——2015 年 9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