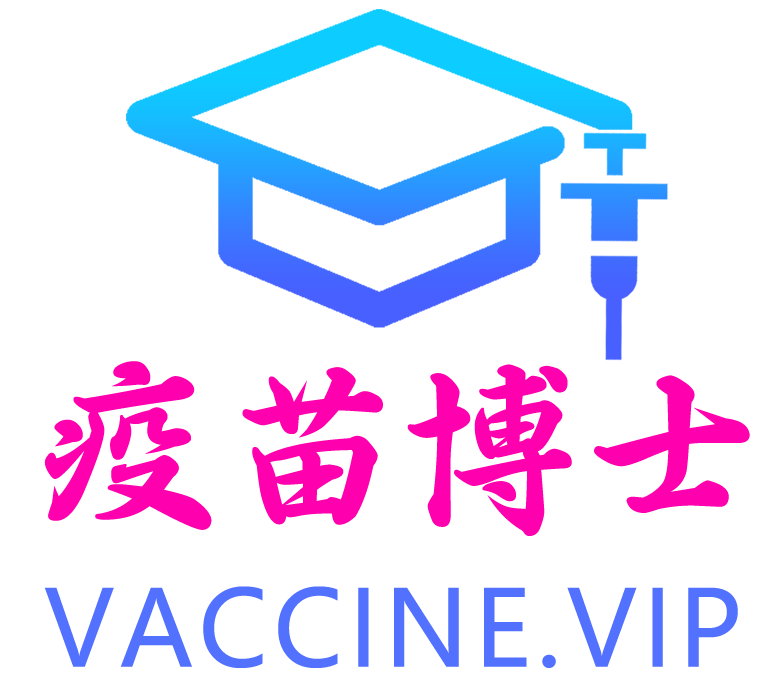Contents
A Policy Outpacing Its Risk: Rethinking the Hepatitis B Birth Dose Mandate
1991 年,当免疫实践咨询委员会(ACIP)首次建议所有婴儿接种乙肝疫苗(UBD)时,美国正面临着一场失控的疫情。20 世纪 80 年代,急性乙肝病例激增,主要集中在有高危行为的成年人中,例如注射吸毒、性暴露或职业性接触受污染血液。乙肝疫苗于 1982 年首次面向成人开放,被誉为生物技术的早期成功案例之一。决策者希望通过向所有婴儿(无论其母亲是否接种)提供疫苗,来保护整整一代人。
正如我们之前的 TrialSite 分析中所探讨的,乙型肝炎仍然是一种可预防的疾病,但在低流行国家为所有新生儿接种疫苗的合理性仍然存在争议。三十年后,全民接种政策仍然是美国历史上覆盖范围最广的疫苗强制接种政策之一。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科学依据却变得参差不齐。尽管该政策最初是为了预防围产期感染而设立的安全网,但在低流行率地区,其合理性却日益受到质疑。大多数高收入国家——包括英国、荷兰和北欧国家——仍然坚持开展有针对性的孕产妇筛查和选择性预防,完全放弃了全民接种。
支持出生时接种疫苗方案的人称其为至关重要的安全网:在产前筛查失败或没有记录的情况下,这是最后一道防线。然而,批评者质疑,鉴于其针对的风险群体相对较小、新生儿安全性信息有限,以及疫苗在降低全国发病率方面的作用尚不明确,对所有婴儿进行疫苗接种是否合理。
如今,这项政策已成为另一个时代的丰碑——备受尊崇,鲜少被重新审视,也鲜少受到质疑。本次回顾将带我们回到这座丰碑前:追溯当初支持为每个婴儿接种疫苗的证据,并根据最新数据,探讨其中有多少证据仍然成立。
追踪衰退——行为还是出生剂量
到 1991 年,当免疫实践咨询委员会(ACIP)扩大其 1991 年的建议范围,建议所有婴儿接种乙肝疫苗时,美国的乙肝发病率已经开始下降。即使在接种过疫苗的新生儿还没到入学年龄之前,20 世纪 80 年代末的发病高峰就已经开始消退。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的监测数据显示,1982 年至 2015 年间,急性乙肝发病率下降了 88% ,从每 10 万人 9.6 例降至 1.1 例。
疫情下降恰逢一系列行为和安全措施的全面变革:献血者筛查、一次性注射器使用、针头交换计划以及安全性行为宣传——所有这些措施都针对造成大部分新增感染的成年人群体。随着医院开始常规接种新生儿疫苗,成人疫情高峰已过。 下降幅度最大的是 20 至 39 岁的成年人 ,而不是刚刚进入疫苗接种时代的婴幼儿。
然而,ACIP 早期发布的总结报告模糊了这种区别。报告将全国感染率下降的曲线与新的婴儿疫苗接种计划并列呈现,暗示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这种关系从未得到证实。事实上,成人间传播的下降早于接种疫苗人群进入青春期的年龄。
这并非暗示疫苗无关紧要——它几乎肯定能预防乙肝病毒阳性母亲所生婴儿的围产期感染,尤其是在与乙肝免疫球蛋白(HBIG)联合使用时。ACIP 自身的策略强调,在母亲感染状况不明或检测结果延迟的情况下,出生后 12 小时内接种疫苗可提供必要的保护( Mast EE 等,MMWR 2006;54(RR-16)) 。
然而,全国数据显示, 1990 年至 2002 年间,急性感染率下降了约 67% ,其中 0-19 岁和 20-39 岁年龄段的降幅最大。尽管 20 世纪 90 年代婴儿疫苗接种覆盖率有所上升,但全国曲线的特征和时间表明,行为改变宣传活动、成人免疫接种和血液安全干预措施至少与新生儿疫苗接种发挥了同等重要的作用。
总体而言,证据表明,全民接种疫苗政策是在疫情开始消退后才实施的。它仍然是一项公共卫生方面的成功举措,但其对整体疫情下降的具体贡献似乎不如此前更广泛的社会和行为转变所起的作用显著。
真正的目标——围产期传播
如果说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全国范围内的疫情确实有所缓解,那么出生剂量疫苗旨在解决的问题就更为具体:围产期传播。乙型肝炎表面抗原 (HBsAg) 阳性母亲所生的婴儿,如果不接受治疗,终生患慢性乙型肝炎的风险高达 90%。正是这条虽小但却危害巨大的传播途径,促使免疫实践咨询委员会 (ACIP) 将其建议作为国家政策,在婴儿出生后 12 小时内接种疫苗。
Ko 等人于 2016 年进行的一项建模研究估计,2009 年美国约有 952 名婴儿患有慢性乙型肝炎——几乎全部是通过母婴传播感染的。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随后估计,随着出生率和孕妇乙肝表面抗原(HBsAg)阳性率的下降,这一数字可能进一步降低,但目前尚未发布更新的全国性估计数据。
这些数字揭示了批评者所强调的悖论:普遍出生剂量疫苗针对的是一个虽小但可识别的风险。围产期感染会带来终身影响,然而真正的高危人群——乙肝表面抗原阳性或未接受筛查的母亲所生的婴儿——仅占美国新生儿总数的一小部分。在产前筛查常规开展且母亲病史可靠的国家,选择性接种疫苗(乙肝免疫球蛋白+对暴露新生儿接种疫苗)就已足够。英国、荷兰和北欧国家在没有普遍接种疫苗的情况下,也都保持了同样低的乙肝发病率。
然而,美国的出发点并非完全出于流行病学考量。ACIP(免疫实践咨询委员会)设立新生儿疫苗接种制度,意在作为一种保障措施——以应对系统性故障,例如筛查遗漏、孕妇就诊延迟或记录缺失。从定义上看,这项政策与其说是公共卫生必需,不如说是一张安全网,确保没有婴儿在繁琐的行政程序中被遗漏。如今的问题不再是这项政策是否有效——它显然能在接触疫苗后预防感染——而是全民接种是否仍然与其所服务的目标人群的风险水平相称。
重新审视 ACIP 估算背后的数据
1991 年,当美国免疫实践咨询委员会(ACIP)准备推行全民婴幼儿乙肝疫苗接种时,其支持广泛接种的依据更多地是模型而非直接监测,而非直接观察。Armstrong 等人(2001 年,《儿科学》杂志) 的一项里程碑式分析预测,在全民接种疫苗之前,美国 10 岁以下儿童每年将有 12000 至 24900 例乙肝感染病例——这一估算基于概率模型和移民人口权重,并预测某些亚群体(尤其是东南亚裔母亲所生的儿童)的风险集中。
后来的研究,包括 Shepard 等人(2005)的研究, 只是重申了“每年数千例”的说法,而没有独立于 Armstrong 的假设之外,重复他所估计的病例负担。然而,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在 2000 年代中期的监测发现,儿童乙型肝炎病例极其罕见,急性病例几乎全部发生在成人身上。到 2006 年,全国发病率已降至每 10 万人 1.6 例,比 1990 年的水平下降了 81%。
Armstrong 等人的估计从未得到直接实证数据的验证,后续监测表明儿童感染人数远低于模型预测。鉴于此, ACIP 在 2018 年的更新中将关注点从假定的广泛水平传播转移到剩余的高危围产期人群——乙肝表面抗原阳性或检测较晚的母亲所生的婴儿——这些人群中仍可能发生传播。
出生安全:数据揭示了什么——以及数据没有揭示什么
与大多数常规免疫接种不同,乙肝疫苗出生剂量是在出生后数小时内接种的——此时婴儿的免疫系统、血脑屏障和肝脏代谢功能尚未完全成熟。正因如此,其安全性一直备受关注。
重组疫苗 Recombivax HB(默克公司)和 Engerix-B(葛兰素史克公司)的上市前试验仅纳入了数百名新生儿,并对受试者进行了数天至数周的随访。结果显示短期耐受性良好——主要表现为轻微的局部反应和短暂的烦躁——但未进行长期的神经发育或免疫学随访( FDA Recombivax HB,2018 ; FDA Engerix-B,2018 )。
上市后监测在提供保障的同时,也揭示了现有数据的局限性。来自疫苗安全数据链(VSD)和疫苗不良事件报告系统(VAERS)的分析未发现一致的安全信号,过敏反应或严重不良事件的发生率仍然极低( McNeil MM 等,Vaccine 2014; 32[14]:1904–1909 )。然而,这些研究大多汇总了所有年龄组的数据,而非专门针对新生儿。专门针对新生儿队列的研究也同样发现,出生剂量后死亡或早期不良事件的发生率并未上升( Eriksen EM 等,Pediatr Infect Dis J 2004 ; Lewis E 等,Pediatrics 2001 )。
动物早期暴露研究的结果因物种而异,且结果不尽相同,可能并不适用于人类新生儿。目前尚无大型前瞻性研究追踪出生剂量后的长期神经发育结果。
总体而言,数十年来接触到的实际数据证实了短期安全性,即使长期新生儿经验研究不足——这一差距需要持续监测和透明报告,而不是引起恐慌。
全球背景——为什么大多数富裕国家拒绝
1991年美国推行新生儿普遍接种疫苗政策时,与其他大多数高收入国家的做法截然不同。乙肝流行率相近的高流行国家选择采取针对性疫苗接种策略——仅为乙肝表面抗原阳性母亲所生的婴儿、与其有密切接触的家庭成员或高危人群接种疫苗——而仅在乙肝高流行国家实行新生儿普遍接种疫苗。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所有新生儿在出生后尽快接种乙肝疫苗 ,理想情况下应在 24 小时内接种,以预防围产期和婴幼儿期传播。然而,各国的具体做法取决于该国的流行病学情况和卫生系统实力。在乙肝低流行国家,如果孕产妇筛查和随访措施完善,选择性围产期预防足以将乙肝发病率控制在极低水平——通常低于每 10 万人 1 例。
另一方面,意大利、罗马尼亚和希腊等基线患病率较高的国家已转向普遍婴儿免疫接种,通常从婴儿出生后6-8周开始。这些差异表明,基于风险考量,同一项全球性建议可能会产生不同的解读:在筛查不足的情况下,普遍新生儿免疫接种可作为一种预防措施;而在孕妇筛查有效的情况下,则应采取针对性保护措施。
对美国而言,ACIP 1991 年的政策体现了这种权衡。全民接种简化了后勤保障,确保不会因筛查不完整或延迟而漏诊婴儿——但也意味着以极低的个人风险为数百万人接种疫苗。其他发达国家则采取了相反的考量,更注重精准性而非普及性。
政策反思——平衡确定性和比例性
美国在几十年前率先推行新生儿乙肝疫苗接种政策,如今它已成为少数几个仍然保留这项政策的高收入国家之一。从实际操作层面来看,该政策卓有成效——事实上消除了母婴传播——但情况已然改变。由于孕妇乙肝表面抗原(HBsAg)阳性率约为 0.3%,与每年数百万剂次的接种量相比,新生儿接种疫苗所能预防的感染病例相对较少。
在支持者看来,这种冗余并非缺陷,而是一种优势——一种保障机制,无论筛查错误、报告延迟或后续工作缺失,都能确保安全。但在批评者看来,这种看似简单的机制却显得越来越不成比例:一项为应对高风险时期而制定的政策,如今在风险微乎其微的情况下仍然有效。这会对风险收益的权衡产生怎样的影响?这场争论与其说是关于科学,不如说是关于治理——社会需要多少确定性,以及为了确保这种确定性,社会能够接受多少效率损失。
在此,美国的普惠式方法和欧洲的选择性方法代表了两种内在的理念:一种侧重于行政上的确定性,另一种则侧重于流行病学上的精确性。两者在各自的体系内都行之有效。如今,政策制定者面临的真正问题是,在孕产妇筛查几乎普及和现代监测手段日益完善的时代,是否应该重新调整保护与比例原则之间的平衡。
证据概览——通过数据重新审视普遍出生剂量政策
下表总结了关于普遍接种乙肝疫苗出生剂量的主要政策主张、支持证据以及文献中指出的剩余不确定性。
| 政策索赔或理由 | 证据表明 | 解释 | 剩余差距 |
| 普遍出生剂量(UBD)推动了美国急性乙型肝炎病例的急剧下降 |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的监测数据显示,1991 年以前发病率有所下降,这主要是由于行为改变和血液筛查等因素导致成年人感染率降低。 | 下降趋势反映的是针对成年人的干预措施,而非针对婴儿的政策。 | 需要更新模型,将行为效应与疫苗效应区分开来。 |
| UBD 对于预防围产期乙型肝炎感染至关重要 | 研究证实,疫苗联合乙肝免疫球蛋白可以预防母婴传播。 | UBD 可确保不会遗漏任何因孕妇筛查失败而漏诊的新生儿。 | 在筛查覆盖率接近全民的情况下,实际获益较小。 |
| 儿童时期的水平传播证明了普遍接种疫苗的合理性 | 早期模型(Armstrong 等人,2001)表明儿童传播率很高,但新的监测发现病例极少。 | 最初的估计可能高估了风险。 | 目前尚无重复研究验证幼儿期传播模型 |
| 出生剂量安全性已得到充分证实。 | 上市前和上市后数据证实了短期耐受性良好;但针对婴儿的长期疗效数据有限。 | 短期安全性得到证实;长期影响仍不确定。 | 婴儿期以后尚无大型前瞻性神经发育研究 |
| 全球共识支持普遍新生儿用药 |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出生后24小时内接种疫苗,但许多低流行国家依赖于选择性围产期预防。 | 普遍接种疫苗主要在高流行地区或未筛查地区实施。 | 普遍策略和目标策略之间的比较结果数据有限。 |
结论——政策与证据
对数据的深入分析支持了大部分批评意见,即美国乙型肝炎病例的急剧下降发生在新生儿接种疫苗时代之前,并且主要归功于行为干预和针对成人的干预措施。该政策所针对的围产期负担确实存在,但规模较小,而且对新生儿接种者的长期安全性随访仍然有限。然而,证据也表明,疫苗本身在接触病毒后通常安全有效,能够预防感染。
因此,事实并非是出生剂量疫苗没有必要,而是其益处已变得高度依赖于具体情况。ACIP 的政策成功地堵住了所有程序漏洞,但在孕妇筛查几乎普及、病毒传播率处于历史低位的今天,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必须重新审视。重新审视疫苗接种比例原则并非反疫苗,而仅仅是循证决策的下一步。
因为公共卫生领域有时最难的问题不是某种方法是否有效,而是它是否仍然需要有效。
© 2025 TrialSite News™。版权所有。
Hits: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