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Science and Soul of Public Health
七个故事,讲述了救生旅程中大大小小的精彩瞬间。

与我的迪内族亲戚一起散步
星期天早上,我们都会去位于迪内(纳瓦霍)乡村的天主教堂。我 13 岁那年,需要提前一个半小时到教堂参加坚信礼课程。于是,我沿着土路走了大约一英里就到了教堂。
我们社区里经常有三四个人和我一起出去。他们就是一些纳瓦霍人所说的“酒鬼”或“喝酒的人”。他们穿越高海拔沙漠地带,试图逃离现实。
虽然他们并非我的血亲,但我把他们当作我的纳瓦霍族亲人——我的叔叔和爷爷。有时,他们默默地走着;有时,他们会分享彼此的故事。
我很享受和他们一起散步的时光,从没觉得这有什么奇怪或不寻常。但大学时,我选修了一门关于童年逆境经历的社区健康课程,才意识到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很不正常。部落社区成员每天都要面对许多被认为是不正常的事情,比如药物滥用、缺水缺电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原住民长期以来所遭受的不平等和歧视的遗留影响。
然而,我逐渐意识到,改变人们对贫困、药物滥用和心理健康问题的负面看法至关重要。我们需要找到基于优势的方法——例如我们的文化、语言和传统知识——并强调这样做带来的益处。
我常常回想起那些散步的时光,以及与社区成员共度的宁静时刻,这些在当今的美国却常常被人们遗忘。
这段经历是我毕生致力于公共卫生、社区和转变观念的原因之一。

在苦难与希望之间
不是我选择了戒瘾治疗,而是戒瘾治疗选择了我。
作为尼日利亚拉各斯一家住院机构的初级医务人员,我亲眼目睹了患者遭受的双重痛苦:戒断反应的煎熬,以及因此而对他们进行惩罚的体制。他们常常被视为“瘾君子”,而不是人。
一位因阿片类药物戒断反应而颤抖的病人恳求医生给他止痛;一位同事却不以为然:“没必要用一种成瘾代替另一种。” 临床医生们鼓吹戒断,仿佛单凭意志力就能重塑大脑。
生物学并非如此运作。患者复发并非因为意志薄弱,而是因为治疗忽略了成瘾的科学原理——物质如何劫持大脑化学物质,以及渴求如何压倒控制力。
今天,作为西非一位开创性的成瘾医学专家,我倡导建立以科学战胜偏见的体系,通过推荐改善药物获取途径的政策,并培训医护人员以证据取代主观判断。在这个体系中,临床医生会在适当的时候提供药物治疗,提供创伤知情护理,并将复发和复吸视为计划缺陷,而非个人失败。护士会问“你感觉如何?”,而不是“你为什么戒不掉?”
然而,有些时刻却能打破日常的沉闷。比如,一位曾经的病人,现在是一名同伴辅导员,递给我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他女儿婚礼上尽父亲职责的场景。“你把我当成一个活生生的人来看待,”他说。
或者,诊所外那位拥抱我的母亲,低声说:“谢谢你相信我的儿子。”
这项工作如同砖瓦般,一点一滴地重建那些被告知不配得到照护的患者的尊严。它弥合了痛苦与希望之间的鸿沟,确保他们不会孤单地走在这条路上。

涟漪效应
大约十年前,我加入了一个志愿者团队,在加州一个以老房子闻名的郊区社区免费发放氡气检测盒和宣传册。我们的团队通过当地卫生部门的倡议联系在一起,大家都有着共同的愿望,那就是积极主动地解决这个公共卫生问题。
我们既不是医生也不是护士——我们只是对预防疾病充满热情。
我们鼓励居民检测地下室的氡气含量,氡是一种无色无味的放射性气体,长期接触可能导致严重的肺癌风险。
一天下午,我们敲响了一户人家的门,发现一位父亲正忙着照顾两个年幼的孩子,看起来筋疲力尽。起初他有些怀疑,但最终还是同意试一试。
一周后,他打电话来说他家地下室的氡气含量远超标准值。他听起来很焦虑,但也庆幸自己及时发现了问题。他联系了一位氡气治理专家,安装了一套简单的管道系统,并配备了风扇装置,将氡气排放到室外。
这种变化显而易见。他敦促邻居们也进行检测。几周之内,又有几户人家发现家中氡含量超标,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教育和预防措施。
那次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社区公共卫生的力量。我们没有提供医疗服务或高科技干预措施,只是提供信息和实用工具。
但这样做,我们帮助人们掌控了自己的健康,并激发了一种超越家庭地下室的集体责任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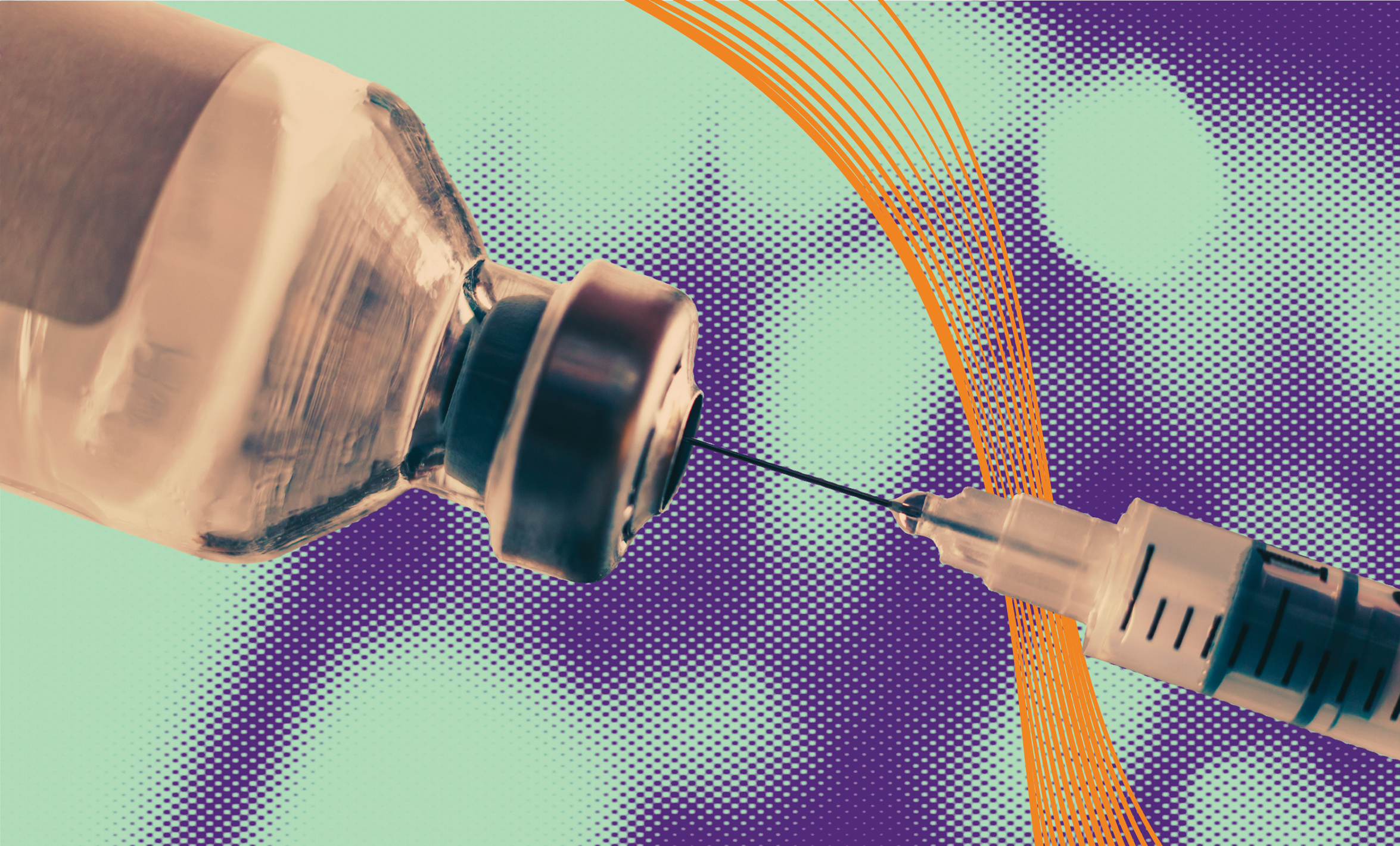
脑膜炎停止发作时
1988 年至 1992 年我接受传染病医生培训时,曾在布朗克斯的蒙特菲奥雷医院和雅各比医院负责儿科工作。每周我们都会接诊一名婴儿或幼儿——大多数都不到 2 岁——患有 B型流感嗜血杆菌感染 。
太可怕了。我的意思是,这些原本健康的婴儿、孩子,竟然都得了脑膜炎。其中三分之一的孩子死了。三分之一的孩子因为脑膜炎出现了发育障碍,比如认知能力受损、听力或视力丧失。还有三分之一的孩子完全康复了。
上世纪 90 年代初引入了 Hib 疫苗,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病例了。
想想看,这种疾病在接种过疫苗的孩子身上已经不会再发生了。
关于疫苗有很多误解。这方面的内容比较复杂——连我都需要查阅资料。所以,普通民众可能不太了解疫苗的工作原理,这并不奇怪。但我必须强调的是,疫苗非常安全。它们都经过了测试,能够挽救生命。

来自贫民窟的梦想
我的祖母玛特罗娜·莱普卡 53 岁时去世了。她死于中风。她是一名售票员 ——在圣保罗的公交车上卖票。她患有高血压,但她没有按时服药,因为那些药是利尿剂,而且她不能经常下车去洗手间。
所以,夺走她生命的并非高血压,而是贫困,是社会环境。
我和祖母、母亲在迪亚德马长大,那是巴西最暴力的城市之一。但我拥有一个了不起的家庭,他们和我一起追逐梦想。我是家族中第一个成为医生的人。或许,我实现了他们的梦想。
我在社区医学实习的时候,我们去了贫民窟,对我来说,那一切都很正常。我就是在贫民窟出生长大的,我并不害怕这些人。相反,他们就像我一样。我可以和他们交流,听懂他们的话,或许也能理解他们的处境。我们对生活的看法不同。我们的生活水平比那些比我们富裕的人要低。
我一直梦想着从事公共卫生工作。它不仅仅是关于细菌和病毒——当然,我也很喜欢研究它们。但它远不止于此。你还需要关注社会环境,观察个体和社会。
公共卫生是一个让我能够将医学、病人护理和健康科学结合起来的途径——同时关注环境,并找出像我一样更容易生病的人。

我的未来在培养皿中
我大概十三岁的时候,莱索托的学校刚添置了一些显微镜。老师让我们去田里,用培养皿装上泥土、干草和水。我们在显微镜下观察,记录下出现的微生物。我们用实验记录本记录观察过程,并把它们画下来。我非常勤奋,每天都观察。周末的时候,我会让姐姐开车送我去学校,这样我就可以查看我的培养物了。她很讨厌这样,因为味道很臭。直到今天,她还会问:“哎呀,你现在又在研究什么腐烂的干草培养物呢?”
我记得当时看到一个让我兴奋不已的微小生物,它有细胞核和鞭毛 。头三天它都没出现,然后就出现了。这真是一次锻炼批判性思维的好机会——这些东西不可能凭空出现,那么它们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运用相同的基本原理来理解是什么使肿瘤细胞变成肿瘤细胞,是什么使肿瘤细胞发生转移,以及其周围环境中发生了什么导致这种情况发生。
我想从基础科学的角度了解疾病。我认为这源于我对那种不起眼的、略显腐烂的干草文化的热爱。

正义已融入我的骨子里
我小时候就听过这些故事——我的曾祖父欧文·惠特菲尔德会把陌生人带回家,给他们洗澡、做饭、铺床。他和我的曾祖母泽拉在密苏里州的家中,无论他们下地干活、组织社区活动、照顾 13 个孩子后多么疲惫,都会像对待皇室成员一样款待每一位客人。
欧文坚信自助之道。1939年,他领导了密苏里州的一场路边抗议活动,为黑人和白人佃农争取权益。那次示威游行是最早的反对经济不公的跨种族抗议活动之一。早在民权运动之前,欧文就挺身而出,站在泥泞的田野里,为公平和尊严而呐喊。
那份传承已融入我的骨髓。
这促使我来到夏威夷工作——虽然远隔千里,但都根植于同样的价值观:正义、公平和关爱社区。
我致力于支持原住民食物系统的恢复,并促进岛屿间的健康公平。我们正在帮助人们重新接触传统的、营养丰富的作物,例如面包果(’ulu)、芋头(kalo)和红薯(’uala)——这些食物在殖民农业和帝国主义剥夺土地、改变水源之前,曾养育了世世代代的夏威夷原住民和太平洋岛民(NHPI)。
食物即良药。因此,我们投资于支持太平洋岛民和移民食品生产商的本地食品聚合商和社区组织。我们正在打造一个“食物即良药”市场,让所有人都能获得符合文化背景、营养丰富的食物。
这项工作意义非凡,它传承了家族传统,延续了欧文和泽拉的愿景——从棉花田到芋头地。
我们继承他们的遗志,因为正义永不消逝。而传承并非继承而来,而是活出自我。
Hits: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