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vercoming Pneumoccocal Meningitis
作者唐尼·齐
这一切都开始于2003年2月的一个星期一早晨。我感觉开始感冒了,但仍然去工作并努力熬过来。回家后,我吃了一些阿司匹林、感冒药,然后洗了个热水澡,试图排汗。周二也类似。星期三,我带着一瓶伏特加和一些橙汁回家。我不喜欢烈酒,我更喜欢冰镇啤酒。但是我喝了10瓶酒,没有宿醉。
周四,我干了半天活,然后生病回家了。星期五,我提前下班去看医生,老板很生气。医生看了看我,听了听我的问题,告诉我我需要在医院想知道是否有人能载我一程。所以我打电话给一位女性朋友,医生给了我一个装在大信封里的断层扫描。
我设法保持清醒,直到我上了我朋友的卡车,大约4:30左右。我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是右转到街上。
我在重症监护室醒来
一个护士看到我醒了,问我知不知道我在哪。我说在医院,看了一眼时钟。“让我猜猜,是星期天早上。”
“不,今天是星期六。”
我对在医院里并不感到惊讶,但我不记得被拉出货车,被脱掉衣服,还有做脊椎穿刺。我想我醒来之前一直是个布娃娃。前几天有一首齐柏林飞船的歌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那是凯迪拉克在电视广告中使用的一首歌。我开始讨厌那首歌(虽然现在我能忍受了)。
在我出院前,我会在重症监护室呆两天,在医院再呆三天。我母亲那边的一个表亲凯丽研究了我的感染情况。这是细菌性脑膜炎,由肺炎链球菌。他告诉我,五分之一的人死于这种疾病,另外五分之一的人身体里有些东西不能像以前那样工作了。
对我来说,是我的听力。我听不到站在我身后的人说话,也听不到他们在和我说话时是否转过头去。就好像我需要看到人们的嘴唇在动。所以我会告诉人们我听力有问题,他们需要直接跟我说。在冠状病毒肺炎期间,人们戴着口罩,我的听力也有问题,但这可能也是在工厂工作48年的影响。
我逐渐找到了应对听力损失的方法,并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它,尽管这需要几年时间。我仍然像一些人一样非常幸运遭受永久性健康问题.
我挺过了肺炎球菌脑膜炎
我在医院的最后一天,他们在我的左臂上插了一根管子,长度足以到达我的心脏。在家里,一名护士来给我注射肝素(一种血液稀释剂)和一些药物。我想她去了大约五次,最后两三次是我给她用药的。然后,接下来的四周我都是一个人。最后,他们叫我去拔管子。他们不想要回剩余的药物,所以我把它捐给了一个非营利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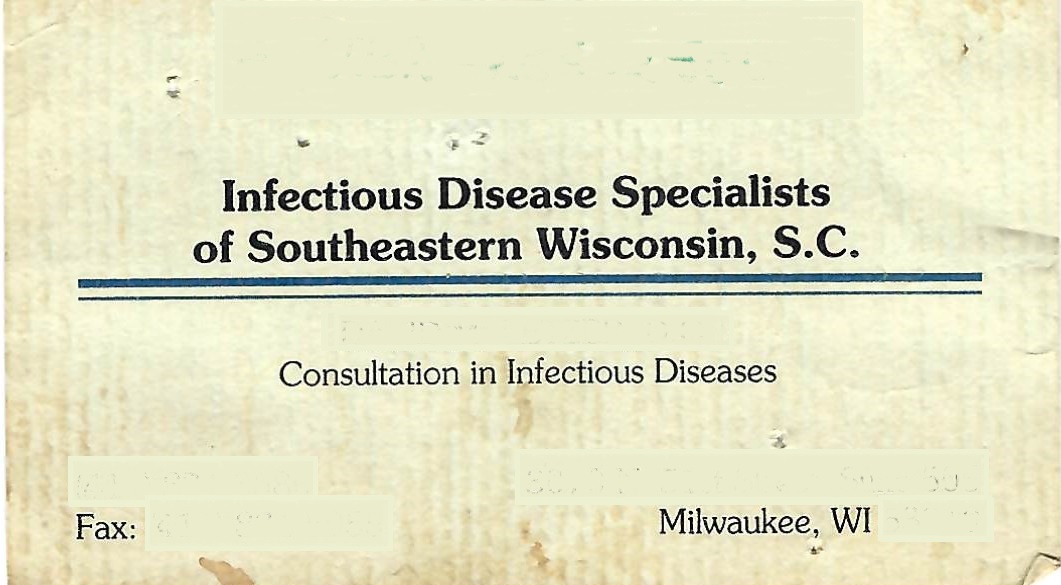
失业五周后,我毫无问题地回去了。我的同事以为我心脏病发作或中风了。当然,我从来没有告诉他们脑膜炎只有一个人问过。我记得听力是唯一有问题的东西。我的老板走到我身后,在我的左边。当我发现他在那里,他的嘴唇在动时,我吓了一跳。他一直在和我说话,我什么也没听到。
我告诉我的老板们,他们需要站在我面前和我说话。他们试图与之抗争。我能听到喃喃自语,一些噪音,一些会提醒我附近有噪音的东西。我没有理会这些噪音,很快,他们站在我面前,引起了我的注意。他们都是混蛋,所以我也是。
我记得和另一位女性朋友苏珊去了酒吧。有一个乐队,音乐很响,我的听力是个问题。苏珊不得不直接对着我的耳朵说话,尽管有时我能读懂她的唇语。我也有一个翻盖手机,我再也听不到了。所以我买了一个音箱比较大的附件,帮助了一些。
我把听力损失的事告诉了我的主治医生。我参加了一个公司的听力测试,并在他的推荐下在另一个地方参加了一次。我不记得结果了。渐渐地,这个问题渐渐消失了,我尽我所能去处理它。我再也没有向医生提起过这个问题。我不得不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
我要说,我今天真的没有脑膜炎的后遗症,不像那些真正受苦或正在受苦的人永久结疤。我还是比较喜欢看嘴唇,但这并不妨碍我和人说话。我可以就任何事情进行长篇大论的谈话。我不认为这是一种残疾。我想不管我有没有脑膜炎,我都会做同样的事情。
我也不想特殊对待。有些人希望得到关注,因为他们身上发生了一些事情。不是我。我有一些问题需要几年才能克服,但我做到了,我不会把它作为一个拐杖。
我从没想过它会发生在我身上
在这一切发生之前,我认为脑膜炎是一种25岁以下的人。我自己的情况开始像感冒或流感,这些只是正常发生的事情。
我确实有一个幼儿园的同学,他得了脑膜炎,19岁就去世了。它成了密尔沃基报纸的头版头条。我记得另一个当地的故事,一个30多岁或40多岁的人得到了它。我想他还活着,因为收音机里没有后续报道或其他什么。脑膜炎是一种在我的城市成为新闻的疾病,或者至少在我们有真正的报纸的时候是这样。
这不是我认为我会得的病,尤其是在我51岁的时候。我的直系亲属都死于癌症。我从不吸烟,但我的父母在家里和车里都吸烟。在酒吧禁止吸烟之前,我吸了很多。在工厂工作,吸入焊接产生的烟雾,我想我还是有可能得癌症。但我从未想过我会得脑膜炎。
当肺炎球菌疾病的疫苗出来时,我很高兴。我会鼓励年轻人去买一个如果有人问起,我会告诉父母让他们的孩子去做VAX。
唐尼·齐是一名退休的工厂工人和脑膜炎幸存者。他的故事,就像这个博客上的其他故事一样,是自愿提交的。如果你想有所作为,请通过以下方式提交你的帖子通过我们的联系方式发送电子邮件给我们. 我们依靠像你这样的真实的人分享经验来保护其他人免受误传。
Hits: 11
